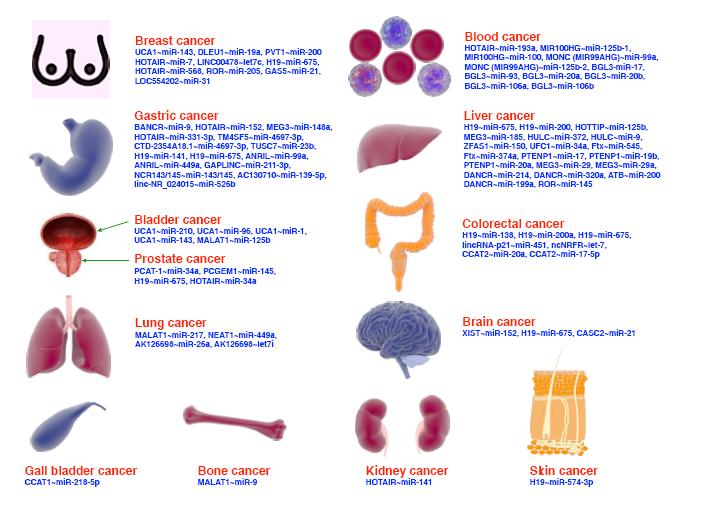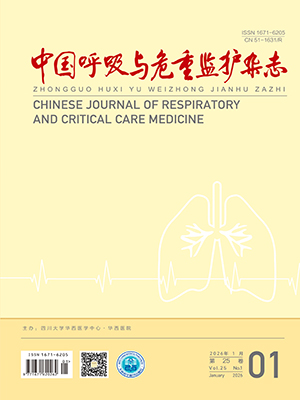| 1. |
Singer M, Deutschman CS, Seymour CW, et al.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finitions for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sepsis-3). JAMA, 2016, 315(8): 801-810.
|
| 2. |
Rudd KE, Johnson SC, Agesa KM,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sepsis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1990-2017: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Lancet, 2020, 395(10219): 200-211.
|
| 3. |
Lin CY, Chen YM, Tsai YH, et al. Association of hypernatremia with immune profiles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 with sepsis. Biomedicines. 2022, 10(9).
|
| 4. |
Qi Z, Lu J, Liu P, et al.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of hypernatremia on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fect Drug Resist, 2023, 16: 143-153.
|
| 5. |
Chand R, Chand R, Goldfarb DS. Hypernatremia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Curr Opin Nephrol Hypertens, 2022, 31(2): 199-204.
|
| 6. |
Rugg C, Strohle M, Treml B, et al. ICU-Acquired hypernatremia is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 inflammation, immunosuppression and catabolism syndrome. J Clin Med, 2020, 9(9): 3017.
|
| 7. |
Wenstedt EF, Verberk SG, Kroon J, et al. Salt increases monocyte CCR2 express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humans. JCI Insight, 2019, 4(21): e130508 .
|
| 8. |
Binger KJ, Gebhardt M, Heinig M, et al. High salt reduces the activation of IL-4- and IL-13-stimulated macrophages. J Clin Invest, 2015, 125(11): 4223-4238.
|
| 9. |
Flierl MA, Rittirsch D, Weckbach S, et al. Disturbances of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and plasma electrolytes during experimental sepsis. Ann Intensive Care. 2011, 1: 53.
|
| 10. |
Braun MM, Barstow CH, Pyzocha NJ.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odium disorders: hyponatremia and hypernatremia. Am Fam Physician, 2015, 91(5): 299-307.
|
| 11. |
Natochin YV, Golosova DV. Vasopressin receptor subtypes and renal sodium transport. Vitam Horm, 2020, 113: 239-258.
|
| 12. |
汪濤. 腸內營養液滲透壓對其輔助治療大鼠潰瘍性結腸炎的影響. 蘇州大學, 2018.
|
| 13. |
Xin Y, Tian M, Deng S, et al. The key drivers of brain injury by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fter sepsis: microglia and neuroinflammation. Mol Neurobiol, 2023, 60(3): 1369-1390.
|
| 14. |
Bayat M, Gourabi H, Khammari A,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function of sc-tenecteplase in the presence of stabilizing osmolytes. J Biotechnol, 2018, 280: 1-10.
|
| 15. |
Lee YI, Ahn J, Ryu JA. Clinical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degree of hypernatremia in neurocritically ill patients. J Korean Neurosurg Soc, 2023, 66(1): 95-104.
|
| 16. |
Hourmant Y, Huard D, Demeure DLD, et al. Effect of continuous infusion of hypertonic saline solution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brain inju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naesth Crit Care Pain Med, 2023, 42(2): 10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