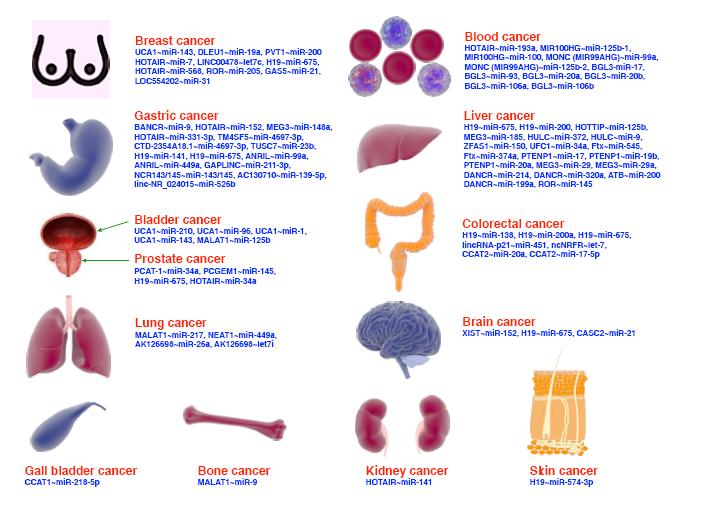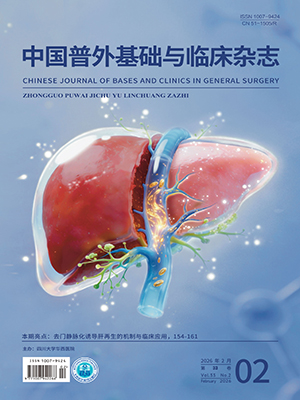| 1. |
Llovet JM, Kelley RK, Villanueva A, et 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at Rev Dis Primers, 2021, 7(1): 6.
|
| 2. |
El-Serag HB. Epidemiology of viral hepatit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Gastroenterology, 2012, 142(6): 1264-1273.
|
| 3. |
Liu J, Fan D. Hepatitis B in China. Lancet, 2007, 369(9573): 1582-1583.
|
| 4. |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2年版). 中華普通外科學文獻(電子版), 2022, 16(2): 81-96.
|
| 5. |
Feng K, Yan J, Li X,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surgical res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Hepatol, 2012, 57(4): 794-802.
|
| 6. |
陳哲宇. 肝細胞癌射頻消融的利和弊.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2, 29(9): 1139-1142.
|
| 7. |
Kulik L, Heimbach JK, Zaiem F, et al. Therapies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wait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epatology, 2018, 67(1): 381-400.
|
| 8. |
Jiang HT, Cao JY. Impact of laparoscopic versus open hepatectomy on perioperative clinic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Chin Med Sci J, 2015, 30(2): 80-83.
|
| 9. |
Yao LQ, Chen ZL, Feng ZH,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recurrence after hepatic resection for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long-term surviv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ce: a 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n Surg Oncol, 2022 Feb 22. doi: 10.1245/s10434-022-11454-y.
|
| 10. |
Wang CC, Iyer SG, Low JK, et al. Perioperative factors affecting long-term outcomes of 473 consecutive patients undergoing hepatectom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n Surg Oncol, 2009, 16(7): 1832-1842.
|
| 11. |
Fan ST, Poon RT, Yeung C, et al. Outcome after partial hepatectomy for hepatocellular cancer within the Milan criteria. Br J Surg, 2011, 98(9): 1292-1300.
|
| 12. |
Rodríguez-Perálvarez M, Luong TV, Andreana L,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icrovascular invas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riability. Ann Surg Oncol, 2013, 20(1): 325-339.
|
| 13. |
Lei Z, Li J, Wu D, et al. Nomogram for preoperative estimation of microvascular invasion risk in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in the Milan criteria. JAMA Surg, 2016, 151(4): 356-363.
|
| 14. |
Feng LH, Dong H, Lau WY, et al. Novel microvascular invasion-based prognostic nomograms to predict survival outcomes in patients after R0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17, 143(2): 293-303.
|
| 15. |
Fu YP, Yi Y, Huang JL, et al. Prognostic nomograms stratify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out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osis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Oncologist, 2017, 22(5): 561-569.
|
| 16. |
Nathan H, Schulick RD, Choti MA, et al. Predictors of survival after resection of earl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n Surg, 2009, 249(5): 799-805.
|
| 17. |
Poon RT, Ng IO, Fan ST, et al.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long-term survivors and disease-free survivors after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study of a prospective cohort. J Clin Oncol, 2001, 19(12): 3037-3044.
|
| 18. |
Jung KS, Kim SU, Choi GH, et al. Prediction of recurrence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FibroScan?). Ann Surg Oncol, 2012, 19(13): 4278-4286.
|
| 19. |
Sun JJ, Wang K, Zhang CZ, et al. Postoperative adjuvant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fter R0 hepatectomy improves outcomes of patients who ha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microvascular invasion. Ann Surg Oncol, 2016, 23(4): 1344-1351.
|
| 20. |
Shen XH, Li HK, Wang F, 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artial hepatectom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orld J Surg, 2010, 34(5): 1028-1033.
|
| 21. |
Whitfield JB. Gamma glutamyl transferase. Crit Rev Clin Lab Sci, 2001, 38(4): 263-355.
|
| 22. |
Ju MJ, Qiu SJ, Fan J, et al. Preoperative serum 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to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ratio is a convenient prognostic marker for Child-Pugh 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operation. J Gastroenterol, 2009, 44(6): 635-642.
|
| 23. |
Sasaki K, Matsuda M, Ohkura Y, et al.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any proportion of poorly differentiated components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after hepatectomy. World J Surg, 2014, 38(5): 1147-1153.
|
| 24. |
Shen J, Liu J, Li C, et al. The impact of tumor differentiation on the prognosis of HBV-associated solit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ollowing hepatectomy: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Dig Dis Sci, 2018, 63(7): 1962-1969.
|
| 25. |
He LY, Xia ZJ, Zhang XY, et al. Tenofovir versus entecavir on the prognosis of hepatitis B-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Int J Surg, 2023, 109(10): 3032-3041.
|
| 26. |
Li L, Li B, Zhang M. HBV DNA levels impact the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microvascular invasion. Medicine (Baltimore), 2019, 98(27): e16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