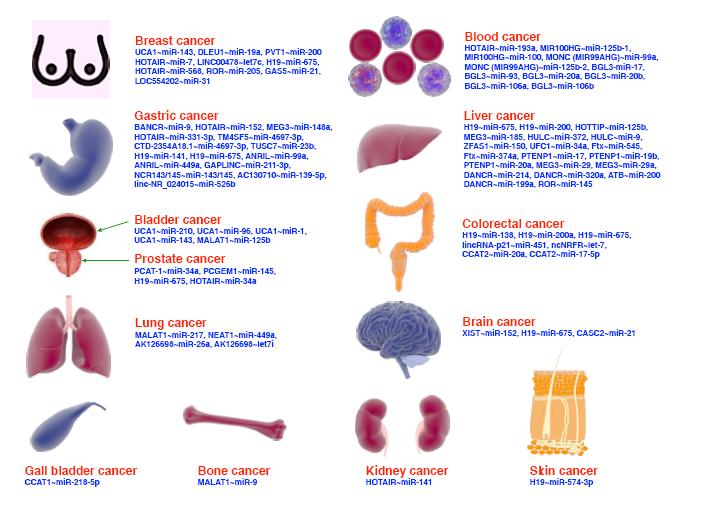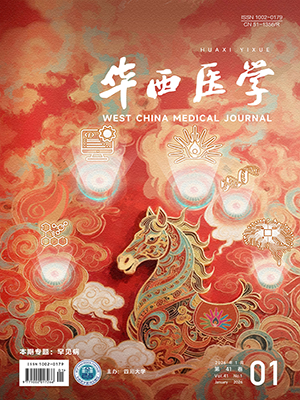| 1. |
Huang C, Wang Y, Li X,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Lancet, 2020, 395(10223): 497-506.
|
| 2. |
Dent E, Martin FC, Bergman H, et al. Management of frailty: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Lancet, 2019, 394(10206): 1376-1386.
|
| 3. |
Fried LP, Tangen CM, Walston J, et al. Frailty in older adults: evidence for a phenotype. J Gerontol A Biol Sci Med Sci, 2001, 56(3): M146-M156.
|
| 4. |
Yamada M, Kimura Y, Ishiyama D,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new incidence of frailty among initially non-frail older adults in Japan: a follow-up online survey. J Nutr Health Aging, 2021, 25(6): 751-756.
|
| 5. |
Subramaniam A, Shekar K, Afroz A, et al. Frailty and mortality associ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tern Med J, 2022, 52(5): 724-739.
|
| 6. |
Zhang XM, Jiao J, Cao J, et al. Frailty as a predictor of mortality among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Geriatr, 2021, 21(1): 186.
|
| 7. |
Dumitrascu F, Branje KE, Hladkowicz ES, et al. Association of frailty with outcomes in individuals with COVID-19: a living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Am Geriatr Soc, 2021, 69(9): 2419-2429.
|
| 8. |
Lee YK, Motwani Y, Brook J, et al. Predictors of COVID-19 outcomes: interplay of frailty, comorbidity, and age in COVID-19 prognosis. Medicine (Baltimore), 2022, 101(51): e32343.
|
| 9. |
De Smet R, Mellaerts B, Vandewinckele H, et al. Frailty and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older adults with COVID-19: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J Am Med Dir Assoc, 2020, 21(7): 928-932. e1.
|
| 10. |
Davis P, Gibson R, Wright E, et al. Atypical presentations in the hospitalised older adult testing positive for SARS-CoV-2: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in Glasgow, Scotland. Scott Med J, 2021, 66(2): 89-97.
|
| 11. |
Wijeysundera HC, Abdel-Qadir H, Qiu F, et al. Relationship of frailty with excess mortal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population-level study in Ontario, Canada. Aging Clin Exp Res, 2022, 34(10): 2557-2565.
|
| 12. |
Salive ME. Multimorbidity in older adults. Epidemiol Rev, 2013, 35: 75-83.
|
| 13. |
Masnoon N, Shakib S, Kalisch-Ellett L, et al. What is polypharmac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efinitions. BMC Geriatr, 2017, 17(1): 230.
|
| 14. |
Gobbens RJ, van Assen MA, Luijkx KG, et al. The 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J Am Med Dir Assoc, 2010, 11(5): 344-355.
|
| 15. |
司華新, 金雅茹, 喬曉霞, 等. 中文版 Tilburg 衰弱量表在養老機構老年人中的信效度檢驗. 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8, 38(16): 4046-4049.
|
| 16. |
Spinato G, Fabbris C, Conte F, et al. COVID-Q: validation of the first COVID-19 questionnaire based on patient-rated symptom gravity. Int J Clin Pract, 2021, 75(12): e14829.
|
| 17. |
Chen P, Nirula A, Heller B, et al. SARS-CoV-2 neutralizing antibody LY-CoV555 in outpatients with Covid-19. N Engl J Med, 2021, 384(3): 229-237.
|
| 18. |
高志華, 楊紹清, Juergen Margraf, 等. Wagnild-Young 心理彈性量表 (RS-11) 中文版的信效度檢驗.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 2013, 21(9): 1324-1326.
|
| 19. |
Rohrmann S. Epidemiology of frailty in older people. Adv Exp Med Biol, 2020, 1216: 21-27.
|
| 20. |
Marengoni A, Vetrano DL, Manes-Gravina E,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D and frail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Chest, 2018, 154(1): 21-40.
|
| 21. |
Hanlon P, Fauré I, Corcoran N, et al. Frailty measurement, prevalence, incidence,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study-level meta-analysis. Lancet Healthy Longev, 2020, 1(3): e106-e116.
|
| 22. |
Palmer K, Vetrano DL, Padua L, et al. Frailty syndromes in persons with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ront Neurol, 2019, 10: 1255.
|
| 23. |
Alvarez-Nebreda ML, Bentov N, Urman RD,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of frailty from the society for perioperative assess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SPAQI). J Clin Anesth, 2018, 47: 33-42.
|
| 24. |
Renne I, Gobbens RJ. Effects of frailty and chronic diseases on quality of life in Dutch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Clin Interv Aging, 2018, 13: 325-334.
|
| 25. |
Evans NR, Todd OM, Minhas JS, et al. Frailty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oncept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for stroke medicine. Int J Stroke, 2022, 17(3): 251-259.
|
| 26. |
Griffith LE, Raina P, Kanters D, et al. Frailty differences across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inequality: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baseline data from the Canadi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ing (CLSA). BMJ Open, 2021, 11(7): e047945.
|
| 27. |
St John PD, Montgomery PR, Tyas S. Social position and frailty. Can J Aging, 2013, 32(3): 250-259.
|
| 28. |
Chamberlain AM, St Sauver JL, Jacobson DJ, et al. Social and behaviour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railty trajectories i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of older adults. BMJ Open, 2016, 6(5): e011410.
|
| 29. |
Welstead M, Jenkins ND, Russ TC,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railty trajectories: their shap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Gerontologist, 2021, 61(8): e463-e475.
|
| 30. |
謝思琦, 馬穎, 崔敏, 等. 老年人心理彈性與生活質量關系的 meta 分析.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22, 36(1): 56-61.
|
| 31. |
Kohler S, Rametta R, Poulter M, et al. Resilience, frailty and outcomes in geriatric rehabilitation. Australas J Ageing, 2020, 39(2): e205-e209.
|
| 32. |
雷鵬瓊, 劉春娜, 高穎, 等. 心理社會因素與社區老年人衰弱的相關性研究. 中國全科醫學, 2018, 21(2): 180-185.
|
| 33. |
Padilha de Lima A, Macedo Rogero M, Araujo Viel T, et al. Interplay between inflammaging, frailty and nutrition in Covid-19: preventive and adjuvant treatment perspectives. J Nutr Health Aging, 2022, 26(1): 67-76.
|
| 34. |
She Q, Chen B, Liu W, et al. Frailty pathogenesis,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older adults with COVID-19. Front Med (Lausanne), 2021, 8: 694367.
|
| 35. |
Wang Y, van Boxel-Dezaire AH, Cheon H, et al. STAT3 activation in response to IL-6 is prolonged by the binding of IL-6 receptor to EGF receptor.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3, 110(42): 16975-16980.
|
| 36. |
Zhu Y, Sealy MJ, Jager-Wittenaar H, et al. Frailty and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from COVID-19 infection among older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dutch lifelines COVID-19 cohort study. Aging Clin Exp Res, 2022, 34(11): 2693-2702.
|
| 37. |
Ali AM, Kunugi H. Screening for sarcopenia (physical frailty) in the COVID-19 era. Int J Endocrinol, 2021, 2021: 5563960.
|